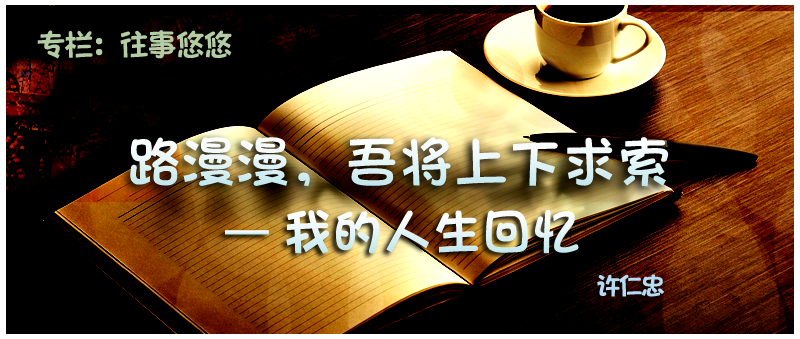
(续)第十三篇 书山有径 学海无涯——我的“大学”
1958年是一个狂热激情的年份,人们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感召下,满腔热忱的投入了各种活动,除了大炼钢铁外,当年总路线提出的要在15年内赶上美国超过英国的“超英赶美”是很激动人心的,作为小学生的我应该是出于知识的浅薄对这个“超英赶美”是很虔诚的,因为根本不知道美国英国的情况,对世界的不了解使我对这一口号深信不疑,我接触到的人们要么跟我一样,要么就是他们知道但就是不说,所以大家都表现出一种狂热的激情,多年之后在逐步知晓了世界才知道当年的狂热激情是多么的荒唐。再有就是到金牛垻的金牛公社金牛大队看万斤高产田,看到密密麻麻的水稻人在上边跳跃,也感到很激动,也是因为对农作物生长的完全不懂不了解,对这种放卫星似的吹嘘也是深信不疑的,在参观到农民在人民公社食堂中的享受各种美食的壮观后,更是深信“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啰。
在望江楼小学读小学的那两年,结识了一位也是住在川大十四宿舍的大哥哥,他给了我集邮的启蒙知识。结识他应该是很偶然的,因为他确实是名副其实的大哥哥,年龄至少大我一轮以上,他家里边的人比较多,他是一个人独居在川大十四宿舍进大门后旁边的一个不大不小的房间中。他是个集邮爱好者,认识他之后他像上课一样的给我讲了很多邮票的知识,向我展示了他集邮的成果,在当年一枚邮票发行的当日,他还带着我到春熙路那一片的成都市邮政总局手把手的教我如何取得邮票的“首日封”。认识了他让我有了很多邮票以及集邮的知识,当然我也一度产生了自己加入集邮队伍的欲望,当然这仅仅是一种欲望而已,因为他告诉我集邮还是一种比较耗费资金的活动,在我当年的家庭状况是不可能有这些资金的,但是十一二岁就有了这些邮票和集邮的知识还是使我感到很欣慰。
我母亲在这两年的时间中,已经不是在四川大学消费合作社工作,在“女人能顶半边天”的鼓舞下她成了工作的积极分子,流动在四川大学成都工学院四川师范学院四川医学院等几个高校的消费合作社工作,因为太繁忙是无暇顾及我和我的兄弟的,几乎是每个月发工资时回家来给我丢下10元人民币,我得用这10元人民币安排好我和我的兄弟一个月的日常生活,那时我10岁多一点,兄弟才4岁多,好在那个时候都是在四川大学食堂里面吃饭,不需要自己煮饭。刚开始的时候因为缺乏计划性,10元钱花得很快,到月底的时候就有些紧张了,不过后来也就慢慢学会了要有计划,要有一个月生活的通盘安排,也就能把一个月我和我兄弟的生活安排的比较妥当了。后来回想起来,这种没有办法的被迫式的10岁就当家的生活历程,也许对我后来几十年的工作和生活都是有所补益的。
也就是从这段时间开始,我逐渐对厨艺其实也就是煮饭有了兴趣便开始习作,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因素有两个,一个是由于范爸爸在四川大学红瓦村食堂工作的原因,所以那两年我在红瓦村食堂与炊事员们厮混得很熟,有不少机会近距离看他们做菜,逐渐产生了兴趣。一道菜在吃的时候你感觉不出什么,其实要做出这道菜是有很多工序的,操作上有很多门道,就像儿时喜欢在皇城垻看那些做小吃的师傅打锅盔做三大炮一样,我也喜欢近距离看这些炊事员师傅如何炒出一道菜,时不时还要向他们问一下我没有看懂的问题。
从10岁开始就对厨艺有所关注有所喜欢除了是因为范爸爸在红瓦村食堂工作的近水楼台先得月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与我父亲当然也包括我的母亲有关。先说说我的母亲吧,这是一位十分能干的女人,1956年她参加工作之前,这位僱农的女儿上得厅堂下得厨房,是一位标准的贤妻良母,并且有自食其力的能力。也许是她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祖父过世得早吧,她从小跟着我的祖母也就是她的母亲在大户人家中厮混,学到了不少江浙皖的东西,特别是做菜。我的母亲虽然娘家是典型的四川人,但川菜却不是她的拿手,她能做出一手精细的口味清淡的江南菜,比如把四川的大青椒掏空放入调配好的口味绝佳的肉馅,先放在油锅中略炸成型,然后在熬好的高湯中慢火煨熟,这道菜吃起来味道简直是不摆了。再就是在冬天的钢炭火盆上,她能支起一套能炖能烤的炊具,在上边烹饪制作各种精美可口的食品。说她是贤妻良母一点也不过分,她除了能在我们住家的光华街街面上销售自己制作的拖帕弥补家用外,每天都会烹饪出可口的饭菜让我送到人民商场当时我父亲工作的地方。
比较遗憾的是1956年她参加革命工作后,用她自己的话来讲就是有组织了,整个人的性态就发生了相当大的几乎是翻天覆地的转变,她由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变成了革命队伍中的“半边天”。自她参加工作之后,家务这些事情她是一点都不屑于了,一心扑在工作上,所以当我住在川大十四宿舍时,很被动的虽年龄仅有10岁还得带着一个4岁的小兄弟自我生活。这时我的父亲因为1957年犯了右倾思想的错误,已经被下放到青白江区新建的成都钢铁厂工作,但他每周还是要回家一次,吃一餐好的饮食是他回家很重要的奢望。我父亲虽然是安徽人,但家乡马鞍山市距江苏的南京以及浙江很近,也许家境败没前还是将就吧,他应该是个典型的“吃货”,遗憾的是他会吃但一点也不会做,这成了我从10岁起开始对厨艺感兴趣很重要的另一个因素,总得有一个人做做饭菜吧,看着家中只有我们父子二人,他吃着我烹饪的饭菜津津有味,我这个做儿子的还是感到有点欣慰。
继续聊聊我的母亲,最大的感悟就是教育与环境可以彻底改变一个人。前面已经说过,我母亲在1956年参加革命工作前,是一个尽善尽美的家庭妇女,相夫教子是她人生的宗旨和目标,1956年他参加工作后应该是她人生的转折点,从那之后她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似的,丈夫和孩子脱离了她的视野,家庭的观念在她心目中不仅是淡漠了应该是消逝了,她一心扑在工作上,一个月仅回家一两次,主要是给我带来生活费,至于我们两个不到10岁的小男孩怎样生存和生活,可能她想的是让我们自生自灭吧,不过这样也好,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后来的几十年中我自己能取得一点成就,多少还是与这种从小就独立得早相关的。我母亲的主要工作是采购,这其实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但她一直完成得很好。当年包括后来的几十年人生经历中,“组织”这个概念是深入了她的脑海的,“我们是有组织可以依靠的”是她几十年来经常念叨的口头禅。我一直在想,她弄明白了这个“组织”的概念是什么没有?因为有这个观念,她一直在家庭生活中表现得很强势,家庭对于她来讲没有依靠和依赖的概念,因为她有组织。产生这个观念一定是教育和环境影响的结果,因为她原来在家庭妇女的生涯中,应该是没有组织这个概念的,参加了工作肯定有人就向她做了教诲:我们现在是有组织了,组织是可以依靠和依赖的,我们的生老病死组织也会管到底的,显然她对此也是信得很深的。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四年左右,到1960年国民经济经济发生困难时她有了一些变化,对工作不再像曾经有过那样的上心了,具体的表现是回家的次数多了,后来也就基本上住在家中与我们生活在一起了。原因嘛后来得知大概有两个,一是她要求加入共产党,但好像一直并不顺利,她最终也没有成为共产党员,二是好像工作中的职务升迁呀似乎经常与她擦肩而过不甚如意。其实她是一个个性很强的人,像她这种个性很强的人,无论是要加入组织还是职务升迁,都会受到一种潜意识的影响,传统的选拔人的标准是不大喜欢像她这种个性比较强又比较爱说话的人的。
不过因为工作的刻苦耐劳,她在薪酬待遇上还是蛮不错的,当年她在比较早的时候就成了4级工,拿到了当年工人中的顶级工资,我的父亲是在她已经拿了若干年四级工工员之后才有这个待遇的,这也是我的母亲瞧不起我父亲的一个很根本的原因。母亲另一个很显著的特点就是她的人际关系特别好,在她工作过的四川大学成都工学院四川医学院四川师范学院等大专院校中,总有一批教授、老师和干部与他有特别良好的关系。
“组织”这个概念在她的头脑和心目中一直是根深蒂固的,“我们是有组织可以依靠的,生老病死组织是要管我们的”一直是她的信念,只是进入90年代后,国营商业的不景气以及她的退休金在社保支付后,特别是后来她的工作单位百货公司事实上己无暇顾及她们这些老职工后,她才逐渐明白这个组织还是有点虚无缥缈的。
(未完待续)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 (80)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衣食住行(256)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衣食住行(255)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衣食住行(254)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衣食住行(253)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衣食住行(252)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衣食住行(251)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 (7)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衣食住行(250)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生活中的繁锁小事(266)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我生活中的繁锁小事(265)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我生活中的繁锁小事(264)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我生活中的繁锁小事(263)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我生活中的繁锁小事(262)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 (119)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我生活中的繁锁小事(261)
- 许仁忠:“口罩”之后香港行(3) - 05/10/24
- 许仁忠:“口罩”之后香港行(2) - 05/09/24
-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 (80) - 05/09/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