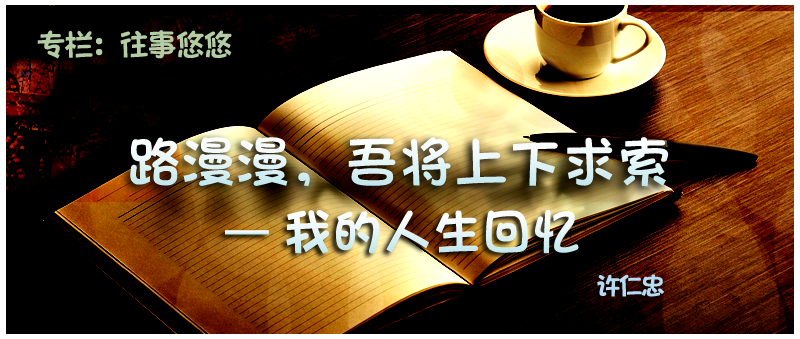
(续)第十四篇 江山易改 秉性难移—我的“城南纪事”
成都七中高中三年的学习生活是过得十分充实愉快的,除了吮吸到最好的基础教育学科知识外,更为重要的是在德高望众的先生们身体力行的引导下,掌握到了不少在学科知识之外的东西,比如自学的能力和逻辑思维方法等等。而更为深入心底的是对自由的领略与期盼,三年的学习生活中,也许是先生们纵容般的默许,我充分体验到了自由的做人做事的乐趣,更是乐在其中的在知识海洋中自由游弋,这个享受的过程让我认识到,只有自由才可能创造出优秀的果实,青年时期的这一认识事实上确立了我这一生中在人生机遇选择上总是把自由放在首位,而事实上我所走过来的一辈子中,也确实实现了方方面面的相对自由。
其实,也正是有了这种相对的自由,我才能在这一生有一定的成就,有一定的所得,我自己很清楚明白,如果没有这种相对的自由,而是被过分的约束和束缚,过分的在他人和他方的管辖之下,所有的这些都是不能取得的。能有这些相对的自由,除了自我的观念就是很追求自由外,也得益于我选择了一个自由度相对较高的职业,那就是高等学校的教师,当然,为了追求和得到这种相对的自由,我也用我可能采取的方法进行了努力,比如在上世纪70年代上半叶,我在成都市金牛区商业局这种机关工作,在当年的政治形势下以及机关工作作风的要求,应该说管理和约束还是比较多比较严的,但我用超乎常人的工作方式和工作结果,使人们乃至整个组织都认为对我的管理和约朿是多余的,从而获得了相对的工作自由。
时间很快的进入1965年下半年,这是我们高中三年的最后一年,我们将要参加1966年的高考,去圆各自的大学梦。也就是从1965年的下半年起,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孕育了好几年的斗争风潮,开始紧锣密鼓的明面化了,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拉开了一场斗争和运动的序幕,半年多的时间中各种各样批判文艺界教育界等文化领域的斗争相继掀开,庞大的舆论宣传告诉所有的人,建国17年来的教育文艺文化等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执行的是修正主义路线,对这种宣传和引导,我与多数国人一样都是深信不疑的,一直坚定的认为应该对这种道路和路线进行深刻批判。
当年我对这种宣传和引导因为一个偶然的特殊原因是特别关注的,因而对它的过程和内容也就特别了解。这个偶然的特殊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这个人在学习学科知识的时候,有一个应该是多数人都没有的奇怪的习惯,就是我在看书做习题特别是做数学题目的时候,不喜欢安静而喜欢喧哗,我喜欢听着收音机播放的音乐和报道,一边听一边看书做习题,恰恰是更多的时候完成题目的灵感会在这种喧闹的环境中突然出现。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尽管已经临近高考,但我在学习中恰好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家中正好当时新购置了一台效果比较好的电子管收音机,我对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所播放的关于文化领域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各种内容,在学习功课的时候却又听得很仔细,这使我深深的接受了当时宣传和引导的全面否定建国17年来文化领域工作的观念,陷入了一种十分左倾的情绪之中。
在这半年多的时间中,我成了一个矛盾体,思维和行为几乎不在一个轨道上。一方面因为我的学习成绩特别优秀,在1965高考题目特别是数学高考题目特别难的背景下,各科科任老师的先生们都在鼓励和嘱托我一定要考出一个好成绩,他们说高考题目越难对优等生是个优势,我自我也在期冀挑战的情绪中感觉在各科学习上达到了一种自由的境界,这种自由的境界一定会出好成绩的。另一方面,在接受了对建国17年来文化领域特别是教育领域没有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宣传和引导下,产生了一种自我疑问自我怀疑,我时不时发自内心的问自己,你接受的是无产阶级文化教育吗?其实在这半年中,由于受到的宣传和引导很深,思想深处总是隐隐的感到会有大事要发生,曾经朦朦胧胧的怀疑过1966年的高考能否如期举行,当然这种冥冥而生的念头是一闪而过的。
真没有想到这种一闪而过的念头,在1966年6月我们即将面临高考的时候一语成谶,由1966年“五·一六通知”掀起并在6月1日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北京大学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揭开序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粹了我们的大学梦,这场浩劫让我和我的同辈人在十多年后己经“三十而立”时才跨入大学门。说实在话对当年停止高考我一点都不感到意外,一切都在顺理成章之中:既然已经说到了17年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主导,停止这一路线的高考这个环节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而对于已经轰轰烈烈掀开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似乎有些躁动,一方面头脑中已经被当时的很多宣传和引导所主宰了,已经认定有一条修正主义路线需要我们去批判,需要我们去树立和捍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另一方面,青少年时间代所形成的对自由的响住和追求,在当年那个合适的氛围中得到了岐形发挥,自由演变成了无政府主义。
躁动和进入角色还有一个戏剧性的因素,那就是我对文字的喜好,特别是对鲁迅和毛泽东文笔的一种欣赏。当年在成都七中我的数理化特别是数学学业优秀,这是很多先生和同学们都予以认同的,但我个人对文字的喜好却鲜为人知,其实在进入高二下学期和高三后,我对毛泽东和鲁迅的文章产生了一种浓厚的兴趣,严格的说这种兴趣不是对文章的内容,而是对鲁迅和毛泽东文章的文笔。对鲁迅文字的喜好有很大一部分来至于我们的语文老师白敦仁先生,他在给我们讲授语文时,很提倡我们去背诵大家的佳作,比如鲁迅先生的《纪念刘和珍君》这样的大块头长文。先生都要求我们去背诵,至于《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这样的短文便更不在话下了。至于对毛泽东文字的崇拜,那是从当年提倡学习毛泽东选集开始的,象《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别了,司徒雷登》这些文章,让喜欢文字的我百读不厌。而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里,相当多的文章文笔都颇有这些味道使人躁动。
从1966年6月开始到1968年底,有一段被称作红卫兵运动的历史。,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下,红卫兵运动几乎成了那场文化大革命浩劫的代名词,这是因为在这两年多的时间中,红卫兵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有作其发生发展落寂结束的过程,这个过程正是那一代青年人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时间,他们被作为冲锋陷阵的先锋完成了该完成的事,发挥了该发挥的作用并且发挥到极致,然后走向自己应该去到的归宿。
严格的红卫兵运动时间应该从1966年8月18日领袖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算起,到1968年7月27日领袖指示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等大专院校为止,实际的红卫兵运动向前应该追溯到1966年6月1日全国大中学校停课闹革命开始,向后应该推移至1968年底1969年初全国中学生响应领袖的号召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在教育为止。我作为当年一个高66级的高中学生,比较深度的参与这场红卫兵运动,运动的洗礼使我脱胎换骨,也更加深刻的认识到了人生与社会,对整个红卫兵运动的由来和发展,还是有所认识和体会的。
其实红卫兵运动无论对外的作用还是内部的组成还是比较复杂的,最早的活动可以追溯的1966年6月初,在那个时间各个学校没有正式的红卫兵组织,但无论是清华北大还是一些中学,都有各种各样的学生运动,它大体从1966年6月初开始,到1966年8月18日领秀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在这两个多月的时间中,学生运动经历了这么几个阶段:先是一种初期的盲动,学生们的大字报铺天盖地的指向了学校的老师们,把他们视为牛鬼蛇神来横扫。很快就有学生中的先知先觉者意识到这种盲目动的问题,他们率先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各个学校的党委领导。在当时的政治背景和同学们的冲击下,各校党委退出了舞台,粉墨登场的是上级派来的文化大革命工作组,这种不适应运动发展的工作组又很快的被学生运动中的佼佼者批评,发生了驱赶工作组出学校运动,学生们的这一系列活动都发生在1966年6月。驱赶工作组的活动被视为是取消党的领导,各个学校的身体力行者被视为右派学生反党而被清查理抹,直到8月上旬公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六条才得以解脱。
(未完待续)
我的更多文章: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 (80)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衣食住行(256)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衣食住行(255)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衣食住行(254)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衣食住行(253)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衣食住行(252)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衣食住行(251)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 (7)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衣食住行(250)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生活中的繁锁小事(266)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我生活中的繁锁小事(265)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我生活中的繁锁小事(264)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我生活中的繁锁小事(263)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我生活中的繁锁小事(262)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 (119)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我生活中的繁锁小事(261)
- 许仁忠:“口罩”之后香港行(3) - 05/10/24
- 许仁忠:“口罩”之后香港行(2) - 05/09/24
-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 (80) - 05/09/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