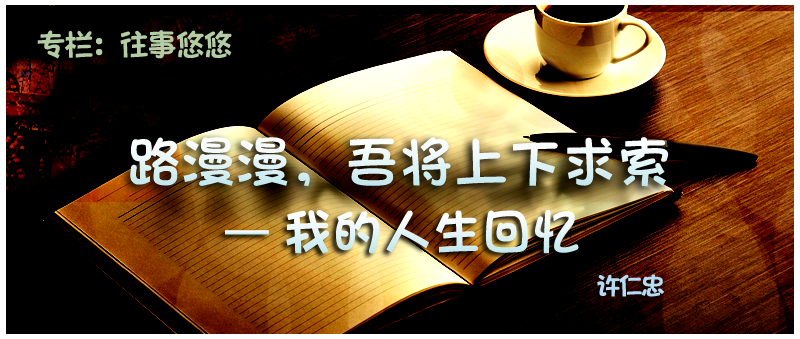
上一篇:我的人生回忆 (2)
(三)在成都七中的五年多
1963年9月,我迈入了成都七中这所重点中学大门,一呆就是五年多。除了高中阶段的三年外,还有两年多是经历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三年是读书学习,后两年多是涉猎了“十年浩刼”早期阶段,所以关于这五年多的七中生活,我也把它分成前三年和后两年多两个阶段来回忆。
上
老三届中的高66级学生,受到了最优秀最全面的基础教育,而在成都七中得到的高中三年的教育和学习,无疑在我的人生中是一个极其重要极其宝贵的学习阶段。
首先是知识的汲取和积累。数理化中的数学,就分成了立体几何、代数、三角和解析几何几科分别学习,高一的立体几何,高二的三角,高三的解析几何,都学了一年,而代数学了三年。物理和化学也是分别学了三年。语文的学习根本没有现在的所谓考试化或客观题标准答案的导向,重点就是阅读和写作。三年中,我和我的同学们在知识的海洋中尽情畅游,吮吸着其精髓和精华。
再就是能力的培养。在成都七中不仅学习到了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和掌握到了终身自我学习的能力。我在七中三年学习中,在各科先生们的言传身教中,在同学们相互间的讨论交流中,在自我学习的能力上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能力的培养不仅是学习能力提升,更多的是社会工作能力的提升。我在进入学校团委担任宣教委员后,负责全校宣传方面的工作,包括参与进行校团委黑板报《青年先锋》的编辑和出版等等。
如果说到成都七中办学特色,这个特色就是自由,自由在七中无时无处不在。学习上,没有上课听不听讲,作业完没有完成的约束和管辖。由于在各科学习上都不错,我在学习上是感到最自由最无拘无束的,完全是在知识的海洋中晃荡。最通常的情况是很少在上课时听老师讲授,而比较离谱的是科目交混,上立体几何课的时候我在写作文,但语文课的时候,又在算一个老是算不清楚的代数题目,基本上是以彼时彼地个人的兴趣行事。这些事情开始我自以为做得很隐秘隐蔽,老师不会知道,其实后来好几位科任老师在私下跟我聊到时,我才知道他们在讲台上对我在课桌上做些什么完全了如指掌。比我年长不到几岁的数学老师谢晋超先生有一次课后直接了当的问我“你今天在课堂上在做啥子?”,我很愕然:谢老师怎么知道我在写作文?因为头天晚上读了毛主席《别了,司徒雷登》的文章,十分兴奋与激动想就另一件事写一篇学习模仿主席文笔的作文!谢先生当时笑眯眯的说:“我看你在下边,神态已经完全进入了角色,比我在讲台上讲课更专注更激动!”。后来我在当了老师之后才明白,任何一位合格的老师,他在课堂上讲的都是大多数同学需要听需要讲的东西。所以,在学习上我是充分感悟到了七中的自由是多么的美好多么的令人神往!
学生干部社会工作的自由度也相当大。比如我负责七中的宣传工作,几乎没有人告诉我该做什么怎样做。做什么得自己去考虑去设计去规划,至于怎样做那更是你自己的事了。记得高二上学期,按当时的政治形势,都在展示人们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热况。于是作为团委宣传委员的我,便提出是不是七中也弄一个集中展示同学们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展览室。整项事情仅仅是在团委工作会议上提出并得到赞同,后来具体怎么弄就没有人管了,一间教室布置出来的这个展览室,无论是里边的陈列品,还是其中的文案语言,都是我组织对这项工作感兴趣的同学们完成的,好像当时做什么事也不需要得到什么人什么部门的批准。当年七中有一个传统的黑板报,命名为《青年先锋》,一位同学在寝室里看到另一位同学很精心很认真的在刷他的皮鞋,就写了一篇文章把这件事视为是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作风,稿件投到了《青年先锋》,登出去后一时引起轩然大波,马上有同学以“刷皮鞋就是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吗?”投稿《青年先锋》,也把它登出去了。于是,在好几期的《青年先锋》上,分别发表了很多就“什么是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为主题的讨论文章。现在回想起来,这项工作当年做的很自由,没有什么校领导呀老师呀来干预同学们的这种自由讨论。有了这种自由的氛围,事情往往做得比期望的更好!
当然,自由之余也不是没有烦恼的,欢悦总是随时与忧虑相伴相随。从1963年到1966年这几年,国内政治舆论的大环境肯定也影响到七中学子的中学学习生活,我自己也难于脱逃。从1964年初开始,一种“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的舆论在全国提倡与蔓延,其中最主要的是对大中学生这种青年群体的说教。这实际上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阶级分析法对青年人特别是青年学生的煎熬和蜕变,这三句话吧,讲得面面俱到,所有的人都在其中。首先是有成分论,所以家庭出身好坏十分关键,然后不唯成分论,既给了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以希望,同时又警示家庭出身好的人也不是进了保险箱,最后的重在政治表现,更是说所有的人一切之一切,你的现实表现才是最重要的。于是在这三句话的魔咒之下,几乎所有的青年学生都陷入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忧思般反省之中。如果说家庭出身好的人因其先天优势而忧患较少一点,或者说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因为前景堪忧忧患也少一点的话,那么那种表面上看家庭出身不错,但实际上存在着一种隐性麻烦的人,忧患和煎熬更更多了。若干年后事过窗户打开时,大家才明白,有这种情况的青年其实占着多数。因为他们的父母辈,在解放前国民党统治的二十多年中,即便是出身很好,比如是工人吧,难免在当时的环境下,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之类的,或者曾经进到胞哥青红帮混过,又如是革命干部吧,有可能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做过与国民党共事的荣生。有这种家庭出身背景的青年人,在过这三句话时特别煎熬:家庭出身很好在明处,父母辈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自己又不是很清楚,但大與论大环境期望着你能去揭发父母辈的阴暗面,在批判和自我批判中得到新生。而我就遇到了这种情况:我的父亲的成分是工人,母亲的成分是僱农,应当很好。但很不幸,父亲在57年反右时,因为健言说了一些不合时宜的话,好在因为是工人,没有被划成右派分子,但被内部定了一个工人阶级中的右倾思想。于是,这就成了一个需要我去揭发去批判去提高的问题,当时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对政治上的患得患失是特别严重的,我也跟其他有这种情况的人一样,陷入了一种特殊的忧虑和煎熬之中,这种情况一直充斥了1965年全年和1966年上半年,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才得以解脱。
再有的一个烦恼就是当时也很讲究群众路线的说法,凡事无论大小,都要去征求去听取群众的意见,而我就在这种征求群众意见的过程中碰倒了特别滑稽的事,不过后来却成了我的“塞翁失马,安知非福”。那是1964年底,我做了一年多校团委宣传委员后,校方认为我特别适合做七中的学生会主席,有关方面都找我谈了话了,让我由校团委委员去转任学生会主席,我甚至和上届学生会主席都进行了初步的接触。但是按照走群众路线的惯例,校方组织了一次到我们班上征求同学们的群众意见的活动,会议结果大出意外,好像班上同学对我意见很大,使校方颇有点为难而举棋难下。怎么办呢?校方权衡许久,在征求了部分科任老师的意见后,与我进行了交流沟通,当然最后的结果是顺应民意我就不去做下届学生会主席了,象干部能上能下一样,按照几个科任老师的意见,回到班上作了学习委员。刚开始我还多少有点情绪,后来才发现。这个学习委员,比校团委委员学生会主席社会工作事情少多了,于是1965年全年和1966年上半年,我得以全身心的投入学业学习之中,使自己在各学科的学业上有了很好的甚至是惊人的积累和发展。事后感叹,这偶发事件真是一桩“塞翁失马,安知非福”的事呵!
所以,当进入到临近高考的1966年四五月间,因为我的学业比较优秀,关心我的几位科任老师以及交往较多的一些同学,在讨论我的高考目标学校时,把我锁在清华北大北航三所学校之中。我们当年大学的排名是清华北大北航三所学校最优,而在当年的政治环境下,考入北航不仅要有与考入清华北大同样的成绩,还需要政治出身好表现好,因为北航当年是军事院校。在他们的心目中,我是应该报考并会进入这三所学校之一读书的,当然最好是北航,仅管当年的名字很不起眼,叫“北京航空学院”,但受到众多的青年学子和老师家长的青睐。当然有这种愿望和看法的更多是我的科任老师以及与我相交较多的同学,他们除了知道我成绩优秀,更知道我在明面处的家庭出身是工人,而他们不知道的另一面是我的父亲其实是工人阶级中的右倾思想分子。
当年关于我在北大清华北航三所大学中必定进一的美谈或笑谈,若干年后还形成了一个“三元会”典故:一次小范围同学聚会上,大家在忆及当年考大学的情况时,说到我当年应当读清华北大北航之一的情况,突发奇想的提出了这个“三元会”概念。为什么叫“三元会”呢?因为我正好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谈论此话题时两个儿子一个巳进入北大一个巳进入北航读书,女儿当年尚小,同学们都笑称许仁忠你再把女儿送进清华,不是圆了您当年清华北大北航三元会之梦吗?当然,事实上的情况是我的女儿没有进入清华,而是在22岁时读了两个国外硕士,一个英国卡迪夫大学的,一个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的。
(未完待续)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 (80)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衣食住行(256)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衣食住行(255)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衣食住行(254)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衣食住行(253)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衣食住行(252)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衣食住行(251)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 (7)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衣食住行(250)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生活中的繁锁小事(266)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我生活中的繁锁小事(265)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我生活中的繁锁小事(264)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我生活中的繁锁小事(263)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我生活中的繁锁小事(262)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 (119)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我生活中的繁锁小事(261)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我生活中的繁锁小事(260)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生活中的繁锁小事(259)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生活中的繁锁小事(258)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生活中的繁锁小事(257)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衣食住行(249)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衣食住行(248)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衣食住行(247)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衣食住行(246)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衣食住行(245)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衣食住行(244)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教育观念(243)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 (23)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教育观念(242)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教育观念(241)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教育观念(240)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教育观念(239)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教育观念(238)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城南纪事”(237)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城南纪事”(236)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城南纪事”(235)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城南纪事”(234)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城南纪事”(233)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城南纪事”(232)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城南纪事”(231)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城南纪事”(230)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城南纪事”(229)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城南纪事”(228)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城南纪事”(227)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城南纪事”(226)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城南纪事”(225)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城南纪事”(224)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城南纪事”(223)
许仁忠: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的市场化(154)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城南纪事”(222)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城南纪事”(221)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城南纪事”(220)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城南纪事”(219)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城南纪事”(218)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城南纪事”(217)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城南纪事”(216)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城南纪事”(215)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城南纪事”(214)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城南纪事”(213)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城南纪事”(212)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城南纪事”(211)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城南纪事”(210)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城南纪事”(209)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城南纪事”(208)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城南纪事”(207)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城南纪事”(206)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城南纪事”(205)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城南纪事”(203)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城南纪事”(202)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城南纪事”(201)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城南纪事”(200)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 (16)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 (74)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 (43)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 (71)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 (111)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 (132)
许仁忠:19世纪的欧洲科学技术与第二次工业革命 (138)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 (91)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 (78)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 (128)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 (28)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后 记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 (49)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大学”(198)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大学”(197)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大学”(196)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 (15)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大学”(195)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大学”(194)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大学”(193)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大学”(192)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大学”(191)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大学”(190)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 (35)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 (19)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 (75)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大学”(189)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大学”(188)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大学”(187)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大学”(186)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大学”(185)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大学”(184)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大学”(183)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大学”(182)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 (86)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大学”(181)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大学”(180)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大学”(179)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大学”(178)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 (90)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大学”(177)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大学”(176)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大学”(175)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大学”(174)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大学”(173)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大学”(172)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大学”(171)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大学”(170)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大学”(169)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大学”(168)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大学”(167)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大学”(166)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大学”(165)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大学”(164)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大学”(163)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 (48)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 (51)
- 欧州旅游:西南欧(一) - 06/08/24
- 许仁忠:“口罩”之后香港行(3) - 05/10/24
- 许仁忠:“口罩”之后香港行(2) - 05/09/24

